清雍正某年正月,安老爷一行人出京南下,这日途经涿州城,见鼓楼西有座天齐庙香火鼎盛,便也随着人潮来到庙内闲逛。只见正殿之前,百姓们烧完香、磕完头,却把那包香的字纸扔得满地,大家踢来踹去,满不在意。
老爷一见,登时老大的不安,嚷道:“阿阿!这班人这等作践先圣遗文,却又来烧什么香!”说着,便叫华忠说:“你们快把这些字纸替他们拣起来送到炉里焚化了。”华忠一听,心里说道:“好!我们爷们儿今儿也不知是逛庙来了,也不知是捡穷来了!”但是主人吩咐,没法儿,只得大家胡掳起来,送到炉里去焚化。老爷还恐怕大家拣得不净,自己拉了程相公,带了小小子麻花儿,也毛着腰一张张的拣得不了……
这个生动的片段出自晚清小说《儿女英雄传》。故事中,被众人笑作“书呆子”的安学海老爷是一位精通四书五经、深受儒家礼教浸染的道德模范。以现代读者的视角来看,我们似乎很难读懂蹲在香炉前捡拾字纸的安老爷的内心世界;但在明清时期的文学叙事模式之下,安老爷的举动却十分“理所当然”。用作者文康的话来说,安老爷发的这些呆,“倒正是场‘胜念千声佛,强烧万炷香’的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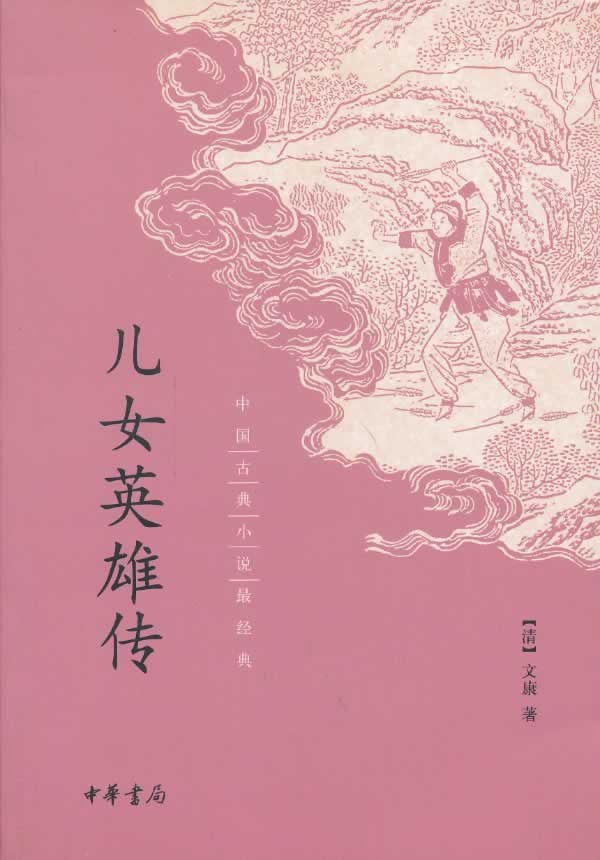
《儿女英雄传》
不肯“作践先圣遗文”的文化心理,早在南北朝时期(5—6世纪)就已出现。著名的《颜氏家训》中明确训诫:“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这种“不敢秽用”的心态,固然出于对圣贤辞旨的敬意,而另一个重要原因亦在于当时“故纸”昂贵,以至于无论官方、民间,都被迫催生出使用“反故”的习俗(即重复利用废纸背面)。南齐的文人沈驎士,年过八十,家中藏书遭焚,不得不亲手用废纸抄写书籍多达两三千卷;敦煌出土的大量文献和宋代用于印书的公文废纸也印证着这段漫长且无奈的“反故”岁月—敬惜字纸的情结,大概正是由此而生。
到宋代时,随着知识获取难度的降低,科举考试向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学子敞开怀抱。纸张和书籍在日渐普及的同时,“高中进士”的追求也成了一种群体心理。一方面,科考内容的广泛性让人们认为无论何种书籍几乎都是有用的,爱护文字纸张成了蟾宫折桂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也促使大量考生把脱颖而出的机运押在各路神佛菩萨上,希望靠平时“行善积德”来换取果报。佛教和道教也纷纷通过各种劝诫故事宣扬敬惜字纸的必要性,尤其是号称“科举之神”、兼掌司命和功名的文昌帝君,顺理成章地成了广大学子的祈求对象。
明代时,随着善书、宝卷(如《文昌帝君劝敬惜字纸文》《文昌帝君惜字功罪律》)的盛行,“科举中第”与“珍惜字纸”被紧密联系起来,由此还催生出一系列笔记小说,为两者的因果关系赋予传奇色彩。最具传奇性的莫若明末小说集《西湖二集》中的赵雄,据传此人天资愚鲁,像《千字文》这样的启蒙读物,赵雄背了好几天,就只记得开篇“天地玄黄”四字,连“宇宙洪荒”都接不下来。可赵雄人虽愚笨,却虔诚发心,把字纸视同珍宝一般,自忖“我一生愚蠢,为人厌憎,多是前生不惜字纸之故。今生若再不惜字纸,连人身也没得做了”。之后,这呆子竟因“阴功浩大”而感动了文昌帝君。在神仙的保佑下,赵雄一路连蒙带撞,奇迹般地考中了进士,最后甚至官至宰相,成了苏轼诗中“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的典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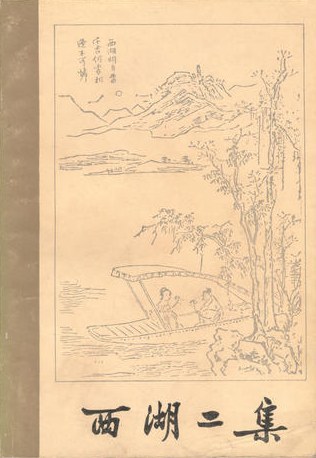
对字纸的敬重不仅能保佑愚笨之人高中,还能惠及子孙后代。在老百姓的认知中,北宋名相王曾就是因其父亲敬惜字纸而得此善报的。传说“凡是污秽之处、垃圾场中,或有遗弃在地下的字纸,王曾父亲定然拾将起来,清水洗净,晒干焚化,投在长流水中,如此多年”。某日,王曾之父梦到孔圣人下凡,称“汝家爱惜字纸,阴功甚大。我已奏过上帝,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使汝家富贵非常”。之后王家果然喜得麟儿,而由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曾子转世投胎的王曾也顺理成章地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
赵雄与王曾在《宋史》中都实有其人,他们宛如“开挂”般的人生经历当然与传奇故事杜撰的“因果”毫不相干,但在明代百姓的心目中,敬惜字纸的行为已然褪去了最初珍惜物资的初衷,转而成为一种获取个人利益的手段,就像《文昌帝君劝敬惜字纸文》中教谕的那样:“考察古今,当发迹之家,高官厚禄,无一不由祖上积功累行,敬惜字纸之果报。”
到了清代,敬惜字纸带来的果报甚至超出求取功名这个单一维度,演变为一切世俗愿望,包括驱鬼、辟邪、免灾、延寿、致富乃至求子。清代笔记小说中,有的人“向不读书而偏知惜字”,除了捡拾字纸,还总能捡到银钱、首饰等意外之财。有人因“平生惜字”,每每遇到飘摇欲坠的告示、广告都要“检藏回家”,因此就算半夜遇到“鬼打墙”,也能如有神助,平安无事。不单字纸有“法力”,字纸烧成的灰也有奇效。据传沿海风俗,船员出海前都要特意去购买字纸烧成的灰烬,包裹好后作为护身符携带出海,一旦遇到怪风、水怪或大可吞舟的怪鱼,把纸灰投入水中即能平安无事。甚至还有“连生五女,八年不孕”的妇女因常年出钱收购字纸而“胎得一子”的奇闻。在释道两教的大力渲染下,清代百姓不仅相信敬惜字纸能保佑“子孙连捷,名登仙籍”,就连“身列仙品,永脱轮回”也不在话下。
这些看似和纸张本身八竿子打不着的“诉求”,都可以通过敬字惜纸得以实现,这恐怕是颜之推订立家训时万万没有想到的。南北朝时被视为贵重物资的纸张,如今被百姓们当作符咒般的“法器”,清洗干净、烧成灰烬,再埋入土中或投入净水,过程中充满了功利主义和仪式色彩。而捡拾字纸也俨然与抄写经文一样,被老百姓简化成了一种积累功德、实现愿望的手段—只要弯弯腰就可做到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晚清光绪年间,出使欧洲列国的郭嵩焘、薛福成等大臣见到西方人“身坐车中,阅新闻纸,随阅随弃,任其抛掷于沟渠污秽之中”的大不敬之举,感到十分震惊。惜纸思想根深蒂固的郭嵩焘在出使期间商讨禁烟和条约事宜之暇,还不忘苦口婆心地劝诫西方官员要爱惜字纸,却发现对方根本不当回事,直言除了“耶稣教书”,“诸字书皆可听从践踏”。回到寓所后,这位中国首位驻外使臣深感洋人社会已经积重难返,还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人心已成积习,则非善言所能入也!”

郭嵩焘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苛责19世纪的欧洲人秽用纸张,毕竟,就算是满腹经纶、一生惜纸的安老爷,也未必能够洞悉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纸价沉浮背后的经济逻辑与信仰变迁。在安老爷、郭嵩焘和广大中国百姓眼中,无论纸上写的是汉字、拉丁文还是阿拉伯数字,爱惜字纸不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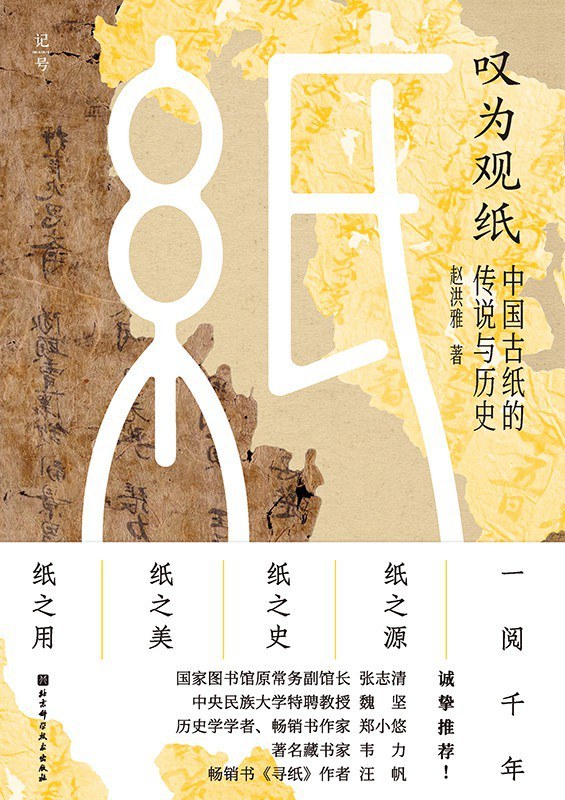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叹为观纸: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 (赵洪雅 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记号Mark,2025年6月版)。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惜纸情结:科举制下的信仰异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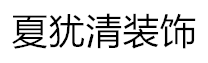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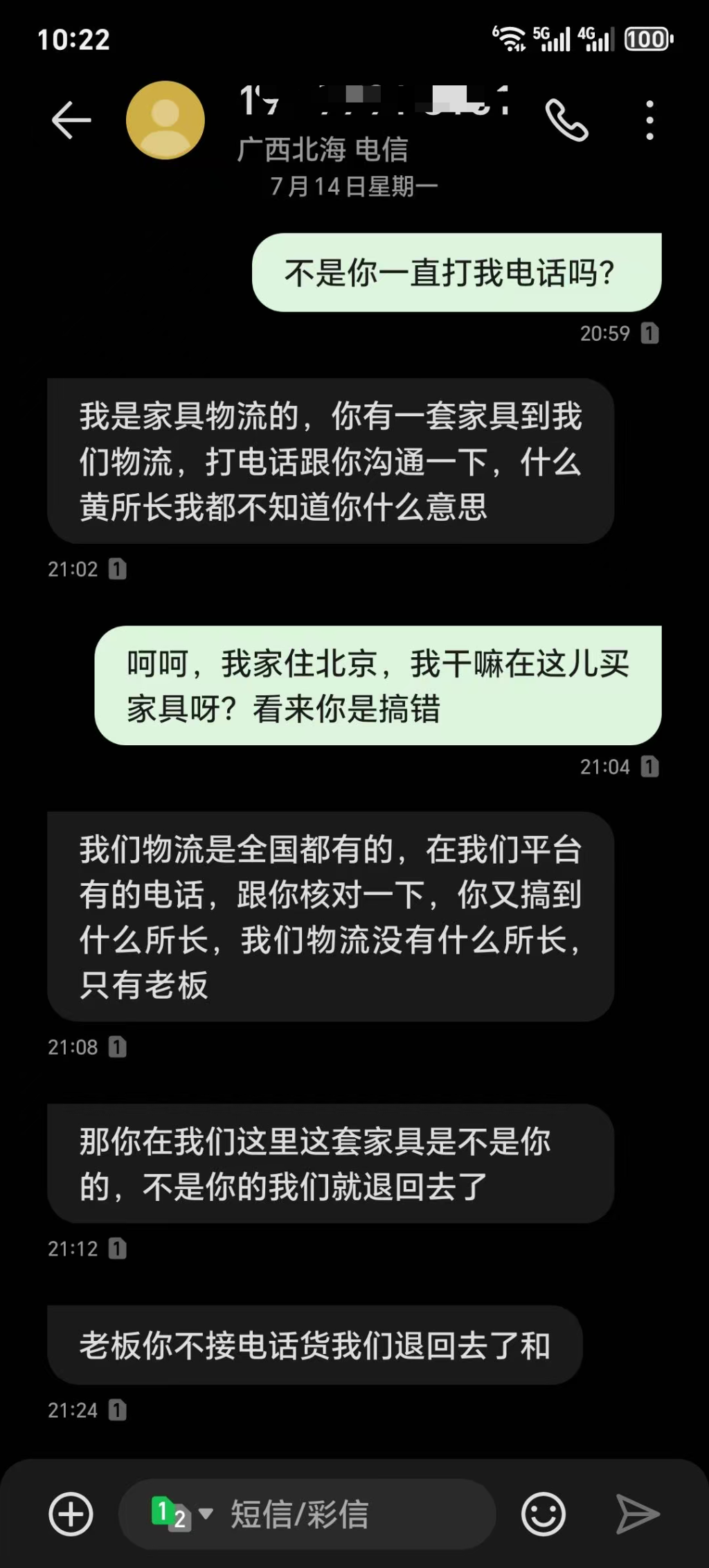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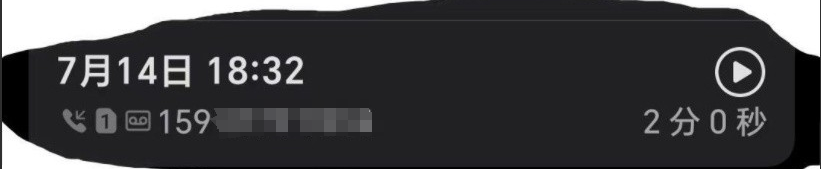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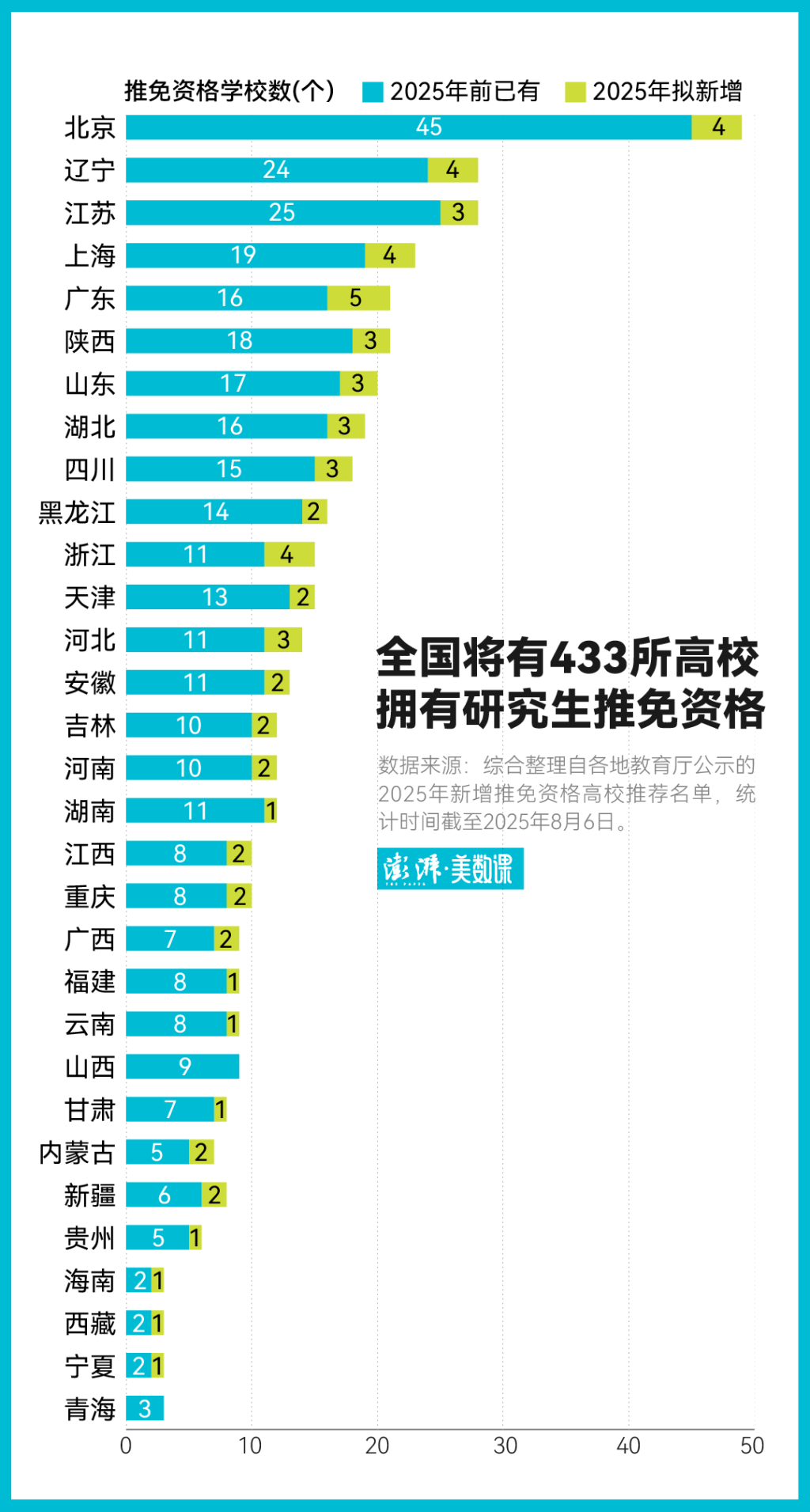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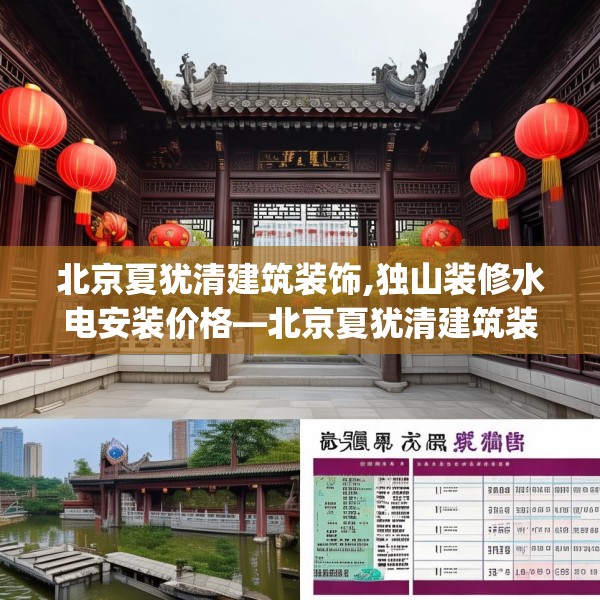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27
京ICP备2025104030号-27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